mastodon @jiangshanghan@slashine.onl
- 6 Posts
- 19 Commen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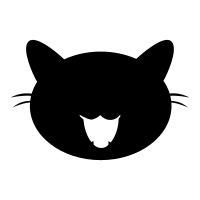 2·1 year ago
2·1 year agono use goodread, we have a similar website in china called douban (it seems like goodread + imdb because users can post about movies they have watched). similar situation. then i heard about bookwyrm and quickly move to bookwyrm for my read memo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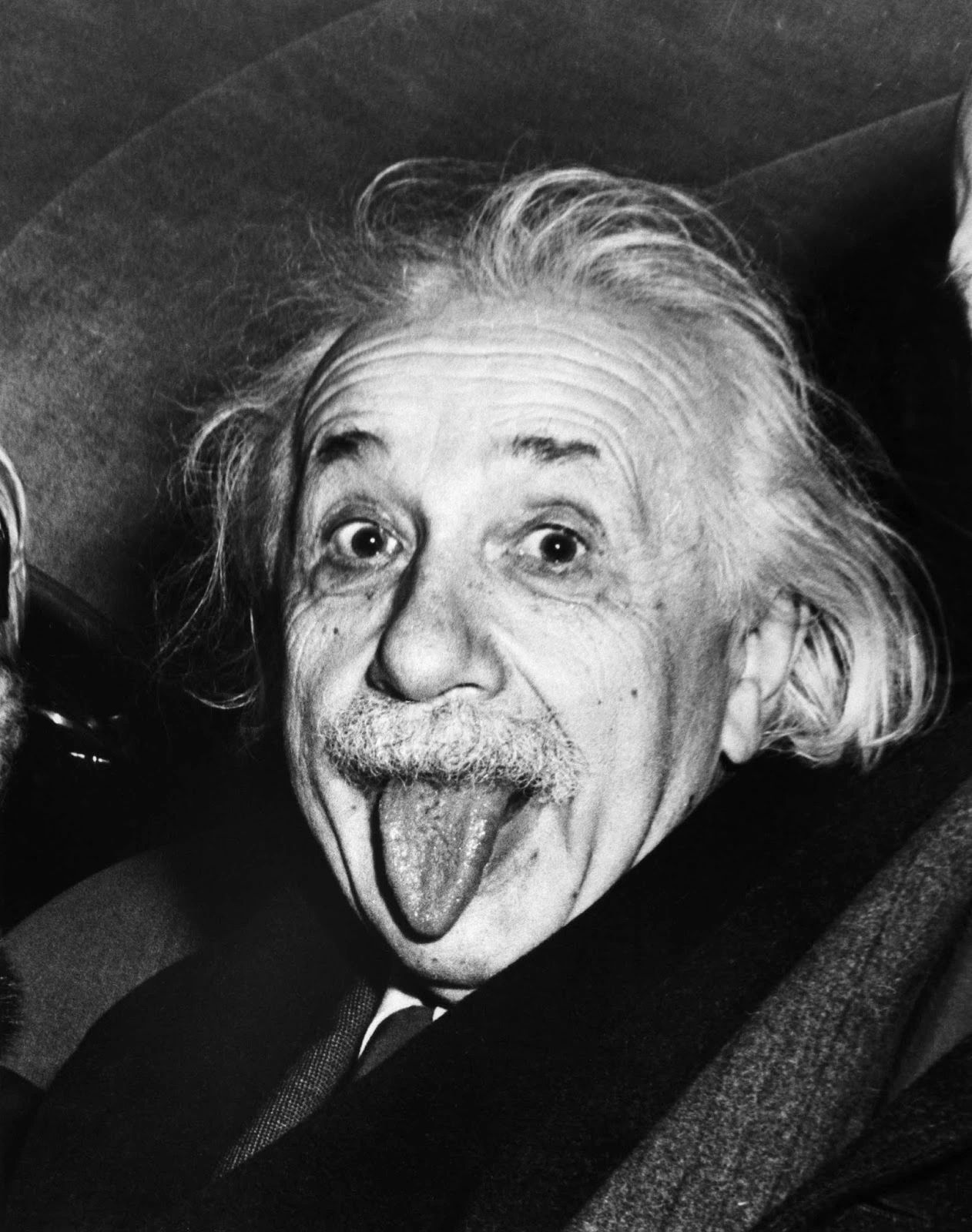 0·1 year ago
0·1 year agono problem. reader helps reader!
塞勒菲斯
从此,库拉尼斯就统治了欧斯·纳尔盖及其周边所有的梦之国度。他在塞勒菲斯和云城塞拉尼安交替处理政务,直至今日。在他的统治下,一切都美满而幸福——不过,在印斯茅斯 (Innsmouth) 的断崖之下,海峡里的波浪却嘲弄着一具流浪汉的尸体,黎明时分,他从半荒废的村庄里踉跄地走出,掉落悬崖;波浪嘲弄着他的尸体,把它推上爬满常春藤的特雷弗塔(Trevor Towers)附近的石滩。特雷弗塔已经被一位开啤酒厂的富豪买了下来,这肥胖而又无礼的富豪正在享受买下绝嗣贵族家的地产的乐趣。
冷气
那恶臭的潦草笔记上写着:“到此为止了,没有冰块了——那个人看了一眼,然后跑掉了。每分钟都在变得更暖和,血肉已经无法再维持下去。我想你知道——我说过的,意志与神经系统还有保存完好的身体能够在器官停止工作后仍能继续运作。这是个好理论,却不能一直持续下去。我没有预见到会发生逐渐的恶化。托里斯医生知道这件事,但那次惊吓杀死了他。他没有办法忍受那些他必须要做的事情——当他留意到我的信,并将我带回来时,他必须在一个黑暗而奇怪的地方找到我。可是器官永远也无法再工作了。事情必须要按我这样来做——人工地保存好一切——你是知道的,十八年前的那个时候,我就已经死了。”
来自遗忘
昨夜,我吞下药,飘入金色的山谷和阴影婆娑的树林。当我到达那古旧的垒壁之前时,看见青铜小门稍稍打开了一点,从门对面射来的炽烈的光,古怪地将扭曲巨树和埋没神殿的顶端照亮。我轻快地向前飘去,心中满怀着对那进去了就不能再归还的国度中的荣耀的期待。
可当门扉大开,药与梦的魔力把我推进门中的时候,我知道所有的美景和荣耀都已终结;在我眼前展开的国度里,没有陆地也没有海洋,只有白色、虚无、无人,同时又无边无涯的空间。因此,我感受到的愉悦比曾经期望过的任何愉悦都强,对现在的我来说,人生只宛如短暂而孤寂的一个小时,我摆脱了这恶魔般的人生,再次融入了故乡的无限、融入了水晶般的遗忘。
一组短篇,偏向于容易解开的谜底,主角最终回落到悲惨的现实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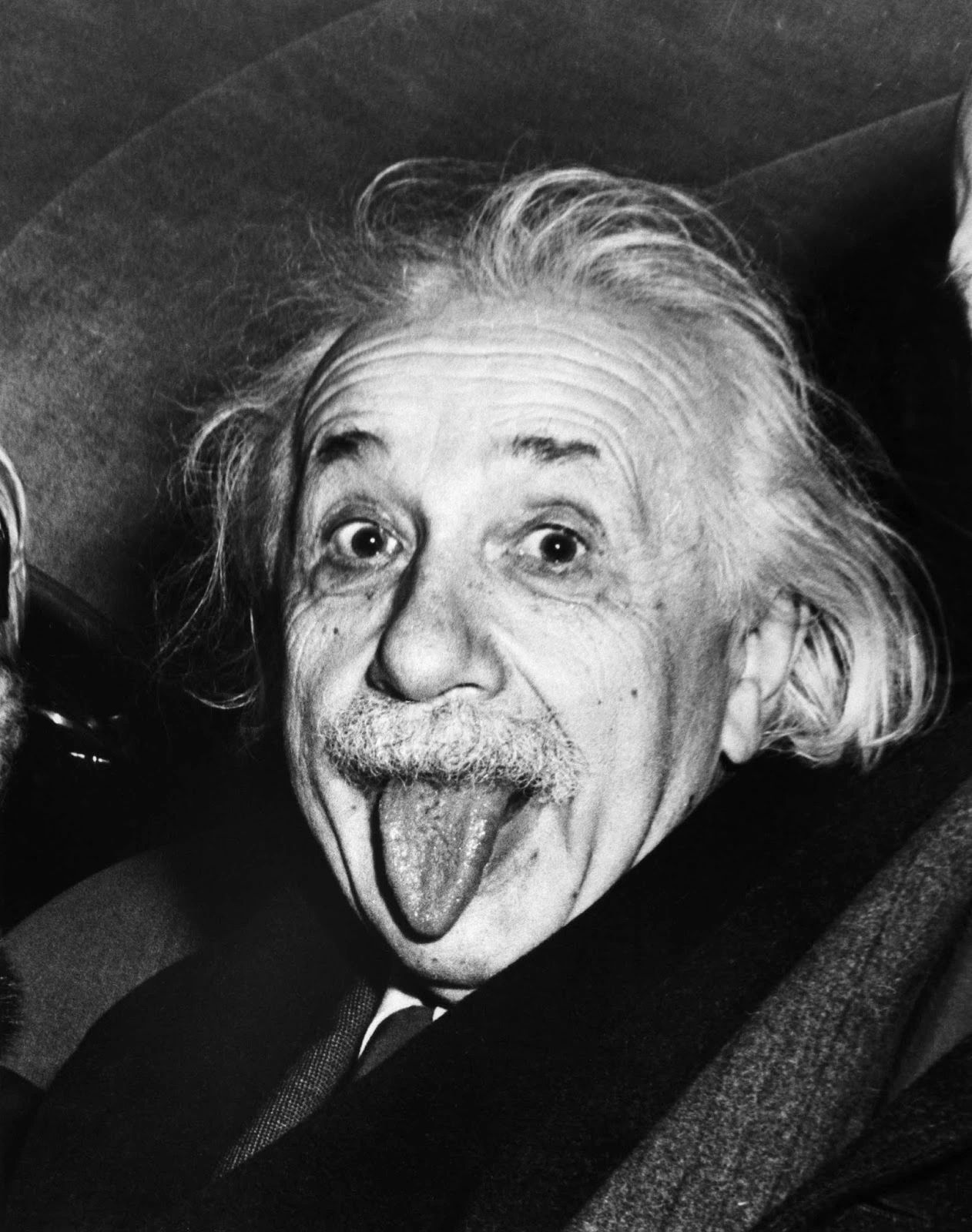 1·1 year ago
1·1 year ago-
The History of Europe:From Ancient Civilizations to the Dawn of the Third Millennium, part 3
-
欧盟政治与外交(赵怀普)
-
The European Union: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John Pinder
-
history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Fabrice Larat
-

 1·1 year ago
1·1 year agoWhen he went to bed, he thought about how sleep was similar to death. When he woke up in the morning, he thought about how pointless it was to get out of bed ;after all, everything he had done was just a plaything in the face of what had to come. He might as well lie there and wait to die.
It’s realistic, even if the quote appears in a story depicting a fantasy character.
Your article really has a deep sense of “telling the old story”, the thoughts of the characters in the story reflect realistic philosophies.

 1·1 year ago
1·1 year agoi use our local library rarely, i think. i can say “very unusual”.
when i was at middle school and university, i use the schools library almost every day.
but now i have more chance to read online. so i do not often go to local library.
sorry about that. i didn t realize you are not belong to lemmy.ml, and i just tried to mark your last post/reply as read. seems i did a wrong click to you!
besides, i can t see up or down user count on my account/post. maybe there was some setting wrong which let me wont see.
翻越睡梦之墙
但随着年龄的增加,他在黎明时分的反常行为似乎也跟着逐渐变得频繁与暴力起来;后来——在他被扭送至精神病院的一个月前——这一行为演变成了一场令人震惊的悲剧,并最终导致他被当局逮捕拘留。事发的前一天下午,他在狂饮过威士忌之后沉沉地睡了过去,但等到第二天接近中午的时候,他极为突然地清醒了过来,并发出了极其恐怖且不同寻常的嚎叫声。这叫声使得邻近的几个人纷纷赶到了他所居住的小屋边——那是一间杂乱肮脏的地方,他与一个和他自己一样污秽不堪的家庭一同居住在里面。接着,他冲进了雪里,高高地挥动着手臂,开始连续地向空中跳去;同时高呼着他决心要前往某个“屋顶、墙面、地板上都有光芒,且响着响亮奇怪音乐的大屋子”。两个中等身材的人试图制止他,但他用狂乱的力量与愤怒抵抗着,尖叫着说出了他的意愿,迫切想要找到并杀死某个“大笑、摇动并发亮的东西”。终于,在突然一拳暂时击倒一个试图制止他的人之后,他陷入了一种恶魔般的嗜血狂喜之中,残忍地尖叫着他要“跳向空中,烧掉所有阻止他的东西。”
“屋顶、墙面、地板上都有光芒,且响着响亮奇怪音乐的大屋子”原谅我只能想到酒吧/KTV……
接着,一段奇异的抒情曲调将我唤醒了过来。四面八方都回荡着和弦、颤动与和谐的心醉神迷,与此同时,在我那令人陶醉的视野中爆发出一番由无上美景构成的宏大场景。我似乎漂浮在空中,而我的四周无数由鲜活火焰构成的高墙、立柱与横梁正在光辉灿烂地燃烧着。它们一直延伸向上,直到那笼罩在无限高处、壮丽得难以言喻的穹顶边。与此同时还有其他一些场景混杂在那幅富丽堂皇的雄伟景象中,更确切地说,它们如同万花筒般旋转着不时取代这幅壮丽的景象。在那之中,我瞥见了旷阔的平原与优美的河谷,高大的山脉与诱人心动的岩穴。所有这一切都覆盖着我那双愉悦的眼睛所能想象出的每一种使得风景更加可爱动人的元素,可却又不仅仅如此,它们完全由某种散发着光辉、虚无缥缈而又柔顺可塑的东西组成的,既像是意识构建的想象又像是实实在在的物质。当我凝视着这一切时,我察觉到自己的大脑控制着这些诱惑迷人的变化;因为每一幅出现在我面前的景象全是我那变化着的念头所最希望看到的景象。在这极乐的国度里,我并没有像是一个陌生人一样踌躇,因为每一幅景象,每一个声音对我来说都是熟悉的;就如同它们在无数个万古之前就已经存在了一样,它们同样也将会一直永存下去。
that s funny. trolled? to who? i did no login since about 1 month ago, i guess. how can we be troll if we off line.
因为全文不长,干脆全部贴来。
阿撒托斯
漫长的岁月从世界上流逝而过,人们的心中失去了惊奇的能力。在灰色的都市里,丑恶而令人反感的高塔直刺天空,在它们的阴影中,没有人会梦见太阳、春天和鲜花盛开的草原。知识从大地上剥除了“美”,诗人只懂用模糊的双眼往自己的内心窥探、将扭曲的幻像歌唱。当这些事情真的降临、当童真的希望永远丧失的时候,有一个人抛弃人生,踏上寻求之旅。他寻找的,正是世界的梦想逃去之所。
这个人的姓名和住所都是属于清醒世界的俗物,微不足道、鲜为人知。我们需要知道的,只是他住在一个被不毛的黄昏永远笼罩的城市,那个城市被高高的壁垒围起。他日复一日地在阴影和混乱中劳苦,晚上回到住处、打开窗户之后,所面对的也不是原野或森林,而只是一个被所有窗口愚钝而绝望地凝视的昏暗庭园。他从窗户里只能看见垒壁和别的窗口,唯有把身体大大地探出窗外,才有可能望到在夜空中运行的微小星辰。一成不变的垒壁和窗口足可把一个经常做梦、读书的人迅速逼疯,因此这房客便夜复一夜地将身体探出窗外,望向高天,只为瞥见一眼那存在于清醒世界和灰色都市彼方的断片。他年复一年地仰望,甚至给那些缓慢运行的星辰取了名字,即使星辰遗憾地滑出视野,他依然在想像中将它们紧紧跟随。就这样,常人无法察觉的诸多秘密幻景终于能被他看见。一夜,巨大的鸿沟上架起了桥梁,萦绕着幻梦的天空越来越近,沉进那孤独的观星者的窗户、化入他周遭的空气,使他与难以置信的惊奇融为一体。
于是在他的屋内,飘浮着黄金尘埃的紫罗兰色暗夜奔涌而入,尘埃与火焰的漩涡从终极的虚空里喷出,又沉淀在来自世界彼方的芳香之中。催人入眠的大海涌了上来,在人的眼睛从未目睹过的阳光的照耀下,游弋在深不见底的漩涡中的奇异海豚和海中女仙现出身形。寂静的无限在入梦者身边缠卷而上,不需触碰从孤寂的窗口里僵硬地探出的身体,便将他轻轻卷起。在不可用人类的历法计量的许多天后,来自遥远领域的浪潮温柔地将他运进梦境——那正是他渴望的梦境、是人类已然失却的梦境。过了无数个周期,潮水只是体贴地让他留在绿色太阳照耀的岸边安眠,那岸边有盛开的莲花的芬芳、有红色的水生植物装点。
工业文明时代都市人住鸟笼既视感。
疯狂山脉 11
剧透折叠(破碎尸体)
我们将两只手电筒都照在了那堆平瘫着的东西上,随后我们就意识到了它们残缺不全的主要原因。虽然它们的身体上有撕扯、碾压、扭曲、割裂的痕迹,但最致命的伤口却是由斩首造成的。四具尸体那带有触肢的海星形头部都不见了;再靠近些后,我们发现它们的头部像是被什么东西给残忍地撕去,或是掉了,而非寻常那样被砍掉的。它们刺鼻的暗绿色液体形成了一滩逐渐向四周扩散的浓浆;但浓浆的刺鼻气味却被后来出现的那种更加奇怪的恶臭给掩盖了;在这儿,这种气味要比我们一路上经过的任何地方更加刺鼻。一直走到那些瘫软尸块身边时,我们才明白那种无法解释的恶臭源自哪里——然后,几乎是在同时,丹弗斯想起了某些非常栩栩如生的雕画,那些雕画里描绘了远古者在二叠纪时期——即距今两亿五千万年前[注]——的历史。紧接着,丹弗斯爆发出了饱受紧张折磨的尖叫。而那声尖叫歇斯底里地回响在这条复刻着邪恶雕画的古老拱顶通道里。
[注:原文为 one hundred and fifty million years ago,但二叠纪的实际时间应为两亿八千万到两亿三千万年前。]
仅在尖叫回响片刻之后,我也恐惧地尖叫了起来;因为我也看见过那些古老的雕画——那些雕画里描绘了包裹在可怕黏液里、瘫倒在地、残缺不全的远古者——它们是那场大规模镇压战争里被可怖的修格斯屠杀并吮吸成恐怖无头尸体的受害者——而此时,我不由得满怀畏惧地敬佩那些无可名状的古代艺术家所完成的工作。即便那些雕画描述的是早已逝去的远古事物,但它们依旧恶名昭彰、如同梦魇一般;修格斯的模样与作为,任何人都不应该目睹,任何生物都不该去描述。就连写下《死灵之书》的阿拉伯疯子也曾紧张地发誓说我们的星球上没有修格斯,只有那些服下迷幻剂的人才能在睡梦中想象出它们的存在。这些无定形的原生质能够模仿任何形状、任何器官、任何动作——它们是一团聚集在一起、带有粘性的肿泡——它们是直径十五英尺、有着无限可塑性与延展性的强韧球体——它们是听令的奴隶,是城市的建造者——它们越来越阴郁、越来越聪明、越来越适宜水陆两栖的生活、越来越懂得如何模仿它们的主人。老天在上!究竟是怎样的疯狂让那些亵渎神明的远古者愿意驱使与雕刻这样的东西?
此时,我与丹弗斯忍受着那些隐约飘散、只有最病态的幻想才能描绘其源头的恶臭;看着那些新近残留下来的、反射着多彩虹光的黑色粘液。这些黏液厚厚地包裹在尸体上,同时也闪闪发亮地黏附墙面上重新雕刻后的那一连串的圆点上。在这一刻,我们最为深刻地了解了广袤无穷的恐惧。我们不害怕那四只不见踪影的远古者——因为我们有理由相信它们不会再伤害我们了。这些可怜的恶魔!毕竟,在同类之中,它们并非恶魔。它们也是人,它们是另一个时代,另一种生物体系中的人。大自然朝它们开了一个残忍的玩笑——将来,如果某些疯狂、麻木或冷酷无情的人想在这片早已死去,或者仍在沉睡的,可怖极地荒野里进行挖掘的话,这个玩笑也会落在他们的身上——这就是它们悲剧的回归。它们甚至都不是野蛮的——说到底,它们到底都做了些什么呢?它们在寒冷里痛苦地清醒过来,发现自己置身在一个陌生的时代——或许一群披着皮毛、狂怒咆哮的四脚动物正在攻击它们。而它们茫然地抵抗着那些疯狂的四脚野兽,同时也茫然地抵抗着一群包裹在奇怪装束与装备里、同样疯狂的白色猿猴……可怜的莱克,可怜的格德尼……还有那些可怜的远古者!直到最后,它们仍怀抱着追求科学的精神——置身在它们的处境中,我们的所作所为又会与它们有什么差别呢?这是何等的智慧!这是何等的坚持!它们面对的是怎样一副难以置信的情景啊!与那些出现在雕刻里的同族与先祖们所面对过的东西相比,它们的遭遇同样难以置信!不论是辐射动物,还是植物,还是怪物,还是自群星降临到这里的东西——不论它们是什么,它们是和人类一样有智性的生物啊!
它们翻越过冰雪覆盖的山峰——在过去,它们还曾在这些修砌着庙宇的山坡上顶礼膜拜;在这些生长着树木般蕨类植物的山麓间漫步,然而现在却只剩下冰雪与刺骨的寒冷。然后,像我们一样,它们发现了这座属于它们的死城与笼罩其上的诅咒。和我们一样,它们也从那些雕画上读到了后来的历史。它们试图与那些还可能生活在黑暗深渊里,自己从未见过的同族取得联系——到最后,它们又发现了什么呢?当我们看着那些包裹在粘液里的无头尸体,看着那些可憎的复刻雕画,看着它们一旁的墙上还带着新鲜粘液的一组组可憎圆点时,所有这些想法闪过了我们的脑海——我们知道是什么东西最终获得了胜利,它们一直栖息在那片满是企鹅的漆黑深渊下,无比巨大的水底城市中。此刻深渊里不祥地喷出了一股翻滚卷曲着的苍白薄雾,仿佛是在回应丹弗斯歇斯底里的尖叫声。
我们不害怕那四只不见踪影的远古者——因为我们有理由相信,它们不会再伤害我们了。这些可怜的恶魔!毕竟,在同类之中,它们并非恶魔。它们也是人,它们是另一个时代,另一种生物体系中的人。大自然朝它们开了一个残忍的玩笑——将来,如果某些疯狂、麻木或冷酷无情的人想在这片早已死去,或者仍在沉睡的,可怖极地荒野里进行挖掘的话,这个玩笑也会落在他们的身上——这就是它们悲剧的回归。它们甚至都不是野蛮的——说到底,它们到底都做了些什么呢?它们在寒冷里痛苦地清醒过来,发现自己置身在一个陌生的时代——或许一群披着皮毛、狂怒咆哮的四脚动物正在攻击它们。而它们茫然地抵抗着那些疯狂的四脚野兽,同时也茫然地抵抗着一群包裹在奇怪装束与装备里、同样疯狂的白色猿猴……
我愿称之为物伤其类。
剧透折叠(遭遇修格斯)
但是,我们并不是站在地铁月台上。我们正站在那堆散发着恶臭犹、如梦魇般的黑亮圆柱前进的道路上;看着那足足十五英尺大小、反射着多色虹彩的前端紧紧地贴着隧道渗涌上来,逐渐提升到匪夷所思的速度,推动着它前方那些来自深渊的苍白水汽螺旋翻腾,并使之再次变得浓密起来。那是一个可怖而又无可名状的东西,比任何地铁都要大——那是一堆无定形的原生质肿泡,闪着隐隐约约的微光。无数只眼睛犹如泛着绿光的脓泡在它的表面不断地形成和分解。而那填满整个隧道的前端向我们直扑过来,将前方慌乱的企鹅尽数压碎,蜿蜒滑过由它与它的同类清理得一尘不染、闪闪发光的地板。耳边依旧传来那怪异、犹如嘲弄般的声音——“Tekeli-li!Tekeli-li!”。最后,我们终于记起,这就是恶魔般的修格斯——远古者独力赋予了它们生命,赋予了它们思想,并赋予了它们可塑的器官与血肉。但它们却没有语言,只能借用那一组组原点来表达——同样,它们也没有声音,只能模仿它们过去主人的声音。
清洁如新的道路……当然, 这是因为有生物行过。
疯狂山脉10
剧透折叠
不过根据通道最前端那规则的形状,以及通道附近分布着更多的企鹅粪便,让我们仍能从诸多大小相等的洞口中挑选出正确的线路。然而我们依旧决定,如果接下来情况变得更加复杂,则要继续采用纸片留下踪迹的方法来进行探索;因为,这时当然已经无法仰赖留在尘土上的痕迹来留下线索了。随着我们继续前进,我们将手电筒的光柱照在了隧道两侧的墙上——接着,我们惊愕地停了下来,因为出现在通道墙面上的壁画已经发生了根本上的变化。当然,我们已经意识到在修筑这些隧道的时期,远古者们已经出现了极大程度地衰落与退化;而且,实际上,我们也注意到了身后那些雕画里的蔓藤装饰已经雕刻得颇为拙劣。但是,这时我们所看到的那些出现在洞穴深处的雕刻却突然发生了一种完全无法解释的改变——这些的雕刻,不论是从完成质量还是从基本特征上来说,都发生了极其巨大的变化,而且雕刻者的技艺也出现了极其严重,甚至是灾难性的衰落与倒退。我们完全无法根据之前看到的那些衰退痕迹推想出它们最后竟会倒退至如此的地步。
这幅严重倒退的新作品显得非常粗糙与拙劣,而且完全没有精细的细节。它的横板深深地陷入了墙内,浮雕最底层的深度与之前遇到的那些圆角方框相同,但浅浮雕的高度却矮了一节,并没有和周围的墙面平齐。丹弗斯认为这可能是二次雕刻的结果——某些雕刻家破坏了先前的雕画,并在上面重新雕刻了新的作品。从内容上来说,这幅作品完全是用来装饰的,上面描绘的图案也颇为普通常见。它由一系列简陋的螺线与折角构成,依旧遵循着远古者传统的五分法数学原理;然而它看起来却完全不像是对这种传统的继承,反而更像是一种拙劣的模仿。除了技巧之外,这些雕刻对于美感的把握出现了某些细微但却完全怪异反常的东西,这种感觉久久地徘徊在我们的脑海,挥之不去——丹弗斯猜测这可能是由于雕刻者费力替换原有壁画,重新雕刻而造成的。它有些像是我们所认识的远古者艺术,但却又有些令人不安的不同;这种混杂的东西让我总是不断地联想起那些按照罗马的方式凿刻出来的难看的巴尔米拉[注]雕刻。走在我们前面的那些东西也曾在这一列雕刻前逗留,因为我们在特征最明显的那一节雕刻下方的地板上发现了一截用完的电池。
[注:Palmyrene 叙利亚中部的一个重要的古代城市,位于大马士革东北215公里,幼发拉底河西南120公里处。是商队穿越叙利亚沙漠的重要中转站,也是重要的商业中心。由于巴尔米拉后被罗马占领,并在提比略统治时期被并入罗马帝国的叙利亚行省,所以那里的雕刻也因此发生了一些变化。]
它由一系列简陋的螺线与折角构成,依旧遵循着远古者传统的五分法数学原理;然而它看起来却完全不像是对这种传统的继承,反而更像是一种拙劣的模仿。
这不是“远古者”而是修格斯做的?
疯狂山脉9
剧透折叠(失踪的物品)
让我坦白一点。我们所看到的那些散落在石堆中的东西全都源自莱克的营地;其中有一些锡罐头——和我们在被蹂躏后的营地里看到的一样,全都以非常奇怪地方式被打开了;许多用过的火柴;三本带有插图并且或多或少被涂污了的书籍;一个空的墨水瓶以及带有绘画和说明的墨水瓶盒;一只被损坏了的钢笔;几块被奇怪裁剪过的皮毛衣物和帐篷帆布;一只包裹着使用说明的、已经用过了的电池;一只帐篷暖炉使用的匣子[注:];还散落着几张折皱了的纸。光是看到这一切就已经够糟了,但是当我们捋平那些皱折的纸张,看到那些涂抹在上面的东西时,事情变得更加可怖起来。之前在营地里发现的那些纸张上也有完全无法解释的圆点,这也许能让我们有所准备,然而,当我们置身在一座噩梦般的城市里,置身在一间存在时间远远长于人类历史的地下室中,再度看到那些圆点组成的图纸时,所产生的惊骇与恐怖仍旧让人无法承受。
[注:a folder that came with our type of tent heater,没见过这个帐篷暖炉,不知道是什么,可能是那种可以抽出来,用来装燃料燃烧的盒子]
也许是发疯的格德尼在这些纸张上模仿了那一组组出现在绿色滑石上的小圆点,正如他在那疯狂的五角星形坟冢上留下的圆点一样;相应地,也许他也曾在路上仓促而简略地绘制好了草图——有些地方精确,有些地方则不太准确——他画出了城市的临近部分,并且从我们之前所经的路线之外的某个用圆圈表示的地方——比如我们在雕刻中看到的圆柱形高塔;或是在高空飞行时瞥见的巨大圆形深坑——一直寻找到了我们所在的这座五角星形建筑里,并曾尝试深入到它下方的隧道中去。
我必须重申,他也许在探索这座城市的时候就准备好了这些草图;因为这些摆在我们面前的图纸显然——和我们手里拿的地图一样——是从这座冰川迷宫中的某些晚期雕画上抄绘下来的。但它所仿制的雕画肯定不是我们曾见过和抄录过的那些。然而一个对艺术一窍不通、笨手笨脚的人不可能用这样一种怪异并且应当被诅咒的方式来绘制这些草图——虽然它们看起来绘制得有些匆忙和粗心,但是其中所体现的技法却可能要比任何它们所仿制的那些已经衰落退化的雕画更加卓越和高超——只有那些生活在这座死城的全盛时期的远古者才具备这样的技巧。
无法解释的圆点 可能是“远古者”的语言,或意外洒的墨水。
然而一个对艺术一窍不通、笨手笨脚的人不可能用这样一种怪异并且应当被诅咒的方式来绘制这些草图
每次看到“怪异并且应当被诅咒的”就觉得太刻意了。
剧透折叠(失踪者的尸体)
我们看到三架雪橇整齐地挤在远处坡道低矮的角落。由于之前一直在向外张望,我们直到此刻才注意到它们的存在。它们是从莱克营地里消失的那三架雪橇。由于过度使用,雪橇已经有些破旧——它们肯定在无雪的石头建筑里以及满是碎石的地表上强行拖拽了很长的距离,而且同样被搬运过许多无法通行的地方。这个时候,它们被小心而聪明地打包捆扎起来,上面摆着我们非常熟悉的那些东西:汽油炉,燃料罐,工具包,口粮罐头,显然塞满了书籍的防水帆布,还有其他一些包裹着其他不明物体的帆布——所有那些从莱克营地带过来的东西。
在地下室里发现了那些东西之后,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准备好看见这样的场景了。然而,其中一块防水布的轮廓依旧让我们觉得有些不安。当走上前去,揭开它的时候,我们才感到了真正的惊骇。看起来,那些东西与莱克一样,也会注意收集典型的标本;因为在雪橇上有两件冻硬、并且被完美保存下来的东西。那些脖颈周围的伤口涂着有黏性的黏合剂,显然是做了修补,而且物体还被小心地包裹起来,避免受到进一步的损害。雪橇上的东西是年轻的格德尼,以及那条失踪的拉橇犬的尸体。
所以死者这是被运走准备做研究用?主角在此因发现地球上还有更厉害的智慧生物而破防?
疯狂山脉7
剧透折叠(浮雕记录城市旧貌)
虽然我们身边的这座真实存在的城市在历经岁月侵蚀之后只剩下了一堆堆奇形怪状的废墟,但是在那些浅浮雕里,这座城市里曾耸立着一簇簇细针般的尖塔,某些圆锥和角锥尖顶上曾有着精巧的装饰,那些圆柱形杆状建筑的顶端曾有着层层叠叠的扇形薄碟。这幅情景与我们即将抵达悲惨的莱克营地时看到的那场可怕而又不祥的蜃景一模一样。当时这座死城的扭曲影像越过无法窥探的疯狂山脉浮现在了我们无知的双眼前——然而作为蜃景的真正源头,这座死城的天际线早在千万年前就已经失去了那些特征。
这是天线吧。
剧透折叠(远古者生活)
远古者们的生活,不论是海中的生活,还是移居陆地后的生活,都足以写上几本大部头的专著。那些生活在浅水区的远古者能最大限度地利用自己生长在头部五条触肢末端的眼睛,并且用非常普通的方法进行雕刻与书写工作——它们用一根尖细的小棍在防水的蜡质表面进行书写。而那些下潜到大洋深处的远古者,虽然拥有一种能散发出磷光的奇怪生物为自己照明,却仍然会利用头部顶端那些多彩的纤毛来补充视力上的不足——这些纤毛似乎具备一种令人费解的特殊感知能力——它们的存在使得所有远古者都能在遇到紧急情况时一定程度上摆脱对光线的依赖。随着深度的增加,它们的书写与雕刻方式也都发生了奇怪的变化。雕画描述了某些看上去像是用化学物在物体表面包裹覆盖的情景——可能是为了固定磷光——但浅浮雕无法向我们做更清楚地说明。在海洋里移动时,这些生物有时会依靠侧旁海百合一般的肢体进行游泳;有时则依靠底端带三角形伪足的触肢进行蠕动。偶尔它们也会利用两对或更多扇子一般可折叠的膜翼进行长距离的滑行。在地面上时,它们会利用自己的伪足进行短程旅行,但偶尔也会利用膜翼飞到极高的地方,或是进行长距离的飞行。由于海百合状的肢体有许多细长的分支,这使得这些肢体在肌肉与神经的调控下变得极端地精细、灵活、强壮与准确——这一特点确保了远古者们在从事各种艺术与手工工作时能最大限度发挥自己的技能与灵巧。
这些生物坚韧得让人难以置信。即使海底最深处的可怕压力似乎也不能伤害它们。除开暴力因素外,似乎只有极少数远古者会死亡,而它们的坟地似乎也非常有限。根据雕画的描述,它们会将死者竖直地埋葬在带有铭文的五角星形坟丘里。看到这里,我与丹弗斯的脑海里都浮现出了某些可怕想法——这让我们不得不再次停顿下来,等待心情恢复平静。另一些雕画显示,这些生物依靠孢子进行繁殖——正如莱克之前推测的一样,与蕨类植物类似——但是,由于它们有着异乎寻常的坚韧体魄与极为惊人的寿命,所以没有必要进行世代更替。除非它们要殖民新的地区,否则远古者不鼓励大规模产生新的原叶体[注1]。幼体成熟得很快,而且需要接受标准高得显然完全超越我们想象的教育。知识与艺术生活占据着社会的主导地位,两者高度发达,并且产生了一套坚持传承了很长时间的风俗与制度。我将在随后的专题论文里对此进行更全面的详述。由于陆地与海洋的居住环境不同,这些风俗也会相应地发生一些细微的变化,但是它们都具备着相同的基础与本质。
[注:prothallia,prothallium的复数。是蕨类植物繁衍后代的中间环。原叶体是由蕨类植物孢子发育而成的独立个体,它有性器官 (母体植物本身没有性器官,只能产生孢子) ,能够产生雌雄配子并受精形成合子,合子会吸收原叶体养分最终发育成新的蕨类植物个体。]
虽然能像植物一样从无机物中吸取养分,但它们显然非常喜欢有机食物,尤其是动物。生活在海底的时候,它们会吞食未经烹饪的海洋生物,但在陆地上,它们会在食用前进行烹饪。这些生物会追捕猎物,也会喂养肉用的兽群——宰杀动物时,它们会使用一种尖锐的武器。我们的探险队之前在化石骨骼上发现的奇怪伤痕就是这些武器留下的。另外,它们能奇迹般地耐受住任何寻常的温度,甚至能不需要保护就能在低于冰点的水中生活。然而,将近一百万年前,更新世的刺骨寒冷让陆地居民不得不开始使用某些特殊的设备,包括一些人造的热源。后来,致命的严寒似乎将它们全都赶回了海里。传说,在很早之前,飞越宇宙空间的时候,这些生物会吸收某些化学物质,然后变得几乎完全不需要进食、呼吸或取暖——但到了冰河时代,它们显然已经忘记了这些方法。现在看来,不管怎样,它们都无法依靠那些人造设备在这座城市里一直安然无恙地生存下去。
由于不需要配偶,而且身体结构比较类似植物,远古者不像哺乳动物那样有着组建家庭的生物学基础。但雕画显示它们依旧会组成类似大家庭的社会单元,根据画面上那些生活在一起的远古者所从事的职业与娱乐活动推断,这些团体是根据空间利用的舒适程度建立起来的,生活在一起的个体都有着相宜的趣味和习性。在布置家园的时候,它们会把所有的东西摆放在巨大房间的中央,将所有的墙面都空出来用于装饰。地上的居民使用一种可能依靠化学电的设备进行照明。不论是在水中还是在陆地上,它们都使用一些奇怪的桌子与椅子,还有一种像是圆柱形框架一样的躺椅——因为它们在休息和睡觉时都是站立着的,仅仅只将身体上触手折叠起来而已——另外,我们还在雕画里看到了一些搁架,上面摆放着一套套带有圆点、用铰链装订而成的平板——那应该是它们用的书籍。
远古者的政府显然非常复杂,而且很可能是社会主义社会,但是单单依靠我们所看到的雕画无法进行任何确定的推断。它们拥有大量的商业活动,不仅在城市内部中进行贸易往来,也会在不同城市之间进行商业交流——某些扁平且带有刻印的小五角星形物件被当作货币进行流通。我们探险队之前也发现了各种淡绿色的滑石,那些较小的样本可能就是这种货币的碎片。尽管在文化上已经是城市文明了,但它们还保留有一部分农业与大规模的畜牧业。矿物开采以及有限的制造活动也都有进行。远古者们经常旅行,但除开在种族扩张时期进行的大规模殖民运动外,它们似乎不太会永久性地移民定居到其他地方。个体在活动时不需要使用额外的辅助设备,因为不论是在水里、地上还是空中,远古者们似乎都能够达到惊人的速度。不过,它们会驱使那些能够负重的野兽为自己搬运重物——在海洋里,它们会驱使修格斯;而后来登上陆地之后,它们则会驱使各式各样奇形怪状的原始脊椎动物。
这些脊椎动物,与无数其他生物——不论动物还是植物,不论海生的、陆生的还是天上飞翔的——都是从远古者们所制造的生命细胞进化发展而成的。那些细胞在脱离了它们注意后,无约束地自行进化繁衍,从而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生命。但这些生命之所以能不受管束地自由发展,主要还是因为它们没有与主宰地球的种群发生冲突。当然,那些带来麻烦的生物全都被远古者们不加思索地灭绝了。但最令我们感兴趣的还是某些年代最晚、技巧也最退化的雕画,雕画里描绘了一种蹒跚滑稽的原始哺乳动物——那些居住在陆地的远古者们有时把它们当作食物,有时则把它们当作娱乐用的小丑——而这种哺乳动物无疑已有了些许模糊的猿猴甚至人类特征。另外,还有一些雕画描绘了远古者们在建造陆地城市时的情形,它们驱使某种巨大的翼龙来搬运建筑高塔的巨型石块——现今的古生物学家对这种翼龙还一无所知。
远古者们在地表经历了各式各样的地质剧变和灾难,却近乎奇迹般地生存了下来。虽然它们修建起来的第一批城市大多——甚至可能是全部——没有熬过太古代[注1],但它们的文明,或者说它们的历史传承却没有出现任何中断。它们最初降落在地球的南冰洋。它们降临的时候,月亮可能刚被地球从南太平洋上甩出去[注2]。根据一幅雕刻在石墙上的地图来看,当时整个地球还位于水面之下。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它们的石头城市逐渐出现在了南极以外的其他地方,并且散布得越来越远。在另一幅地图上,南极点附近已经出现了一块巨大的干燥陆地。显然,有一部分远古者在这片大陆上建造起了一些实验性的定居地,但整个远古者族群的主要中心还是转移到了最近的海底。年代较晚的地图反映了这片巨大陆块的断裂与漂移,同时也描绘了一些分离的小陆地向北移动的过程,所有这些都明显地论证了最近由泰勒、魏格纳与乔利等人所发展起来的大陆漂移理论。
[注1:地球成形到25亿年前]
[注2:此处依据的是19世纪末,乔治·达尔文在研究了地月系统的潮汐演化后提出的最早的月球形成理论。该理论认为月球是从地球分离出去而形成的,并提出太平洋盆地就是月球脱离地球时所造成的一个巨大遗迹。这一理论现在已被撞击假说取代。]
随着新大陆从南太平洋的海底隆起,一系列巨大的变故接踵而至。远古者的许多海底城市被彻底地毁灭了,然而这还不是最不幸的事情。没过多久,另一个种族,一个像是章鱼的陆地种族——可能就是那些出现在传说里、存在于人类之前的克苏鲁的眷族——从无垠的宇宙中降临到了地球上。它们对远古者发动了突然袭击,挑起了一场可怕的战争。一时间,远古者们被全数赶到了海底——考虑到陆地定居点的数量之前一直在增加,这一定是个巨大的打击。后来,双方达成了和解,克苏鲁的眷族能占有那片从海中升起的新大陆;而远古者则仍保留海洋与所有的旧大陆。它们新建了一批陆地城市——当中最为巨大的城市就在南极,可能它们将自己种群最初抵达的区域视为圣地。从这时起,事情回到了以前的模样,南极大陆再度成为了远古者文明的中心,而克苏鲁的眷族之前在南极修建的城市全都被远古者清除掉了。随后,在某个时期,位于南太平洋的那些大陆突然沉没了,一同淹没的还有那座恐怖的石城拉莱耶,以及所有从宇宙中降临到那片土地上的章鱼种族[注]。于是,远古者们再度统治了整个星球,只不过,这时的它们已经有了一些不愿提及的隐隐忧惧。过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之后,它们的城市已经散布到了全球的各个大陆与海洋——因此我会在即将发布的专题论文中推荐一些考古学家利用帕波第的钻探设备在一些广泛分散的地区进行系统的钻探考察。
[注:the cosmic octopi,宇宙章鱼!]
生活在一起的个体都有着相宜的趣味和习性
很符合fedi民的特征!
剧透折叠(修格斯的叛逆)
随着岁月的流逝,远古者们逐步从水底转移到了陆地上——不断出现的新陆块也促进了它们的移民,但那些位于海底的城市却从未彻底荒废。另一个促进它们向陆地转移的原因是修格斯。在海底生活需要使唤修格斯,但它们在培育和管理修格斯时却遇到了新的麻烦。远古者们在雕画里悲伤地承认,随着时间的推移,从无机物中创造新生物的技术已经遗失了,所以它们只能改造那些已经存在的生物。陆地上的巨型爬行动物很容易驯服;但海里的修格斯,不仅能依靠分裂进行繁殖,而且偶尔还会表现出非常危险的智力。一时间,这些东西已成为了非常严重问题。
过去远古者们一直都利用某种类似催眠的技术牢牢地控制着修格斯,令它们坚韧而又可塑的形体变成各种各样临时的肢体与器官;但到了这个时期,修格斯偶尔也能独立地表现出自我塑形的能力,并开始模仿过去那些依照远古者的命令而塑造出来的形状。它们似乎发展出了一个不太稳定的大脑,这颗大脑不仅独立而且有时候会变得非常顽固倔强。它们会附和远古者的愿意,却不总是遵循命令。雕画中的修格斯令我与丹弗斯充满了恐惧与嫌恶。它们通常只是一些粘性胶冻般不定形的块状物,看起来像是一堆泡沫组成的聚集体。当它呈球形时,平均直径约十五英尺。不过,它们的形状和体积总在一个不断地变化——抛出临时的附肢,或是形成某些用于模仿它们主人看、听与说话的器官——这个过程既可以是自发的,也可以遵循远古者的命令。
到了二叠纪中期,大约两亿五千万年前[注],修格斯似乎变得更加危险和倔强了。居住在海洋里的远古者发动了一场真正的战争,试图镇压它们。一些雕画描绘了这场战争,也描述了那些被黏液包裹着的无头尸体——修格斯一般会这样对待它们捕捉到的受害者。尽管这些场景发生在距离我们无穷遥远的过去,但却依旧让人觉得毛骨悚然。远古者们利用一种能够将物质裂解成分子与原子的奇怪武器镇压了反叛的修格斯,并最终取得了完全的胜利。雕画显示,随后的一段时间里,在全副武装的远古者们面前,修格斯变得既温顺又沮丧,就像美国西部那些被牛仔们驯服的野马一样。但在反叛期间,修格斯展现出了新的能力:它们能够离开水体后继续存活了。不过,远古者并没有发展它们的这种能力——因为在陆地上,它们带来的用处远远抵不上管理它们的麻烦。
[注:此处原文为the middle of the Permian Age, perhaps one hundred and fifty million years ago, Permian Age,二叠纪应该为两亿八千万到两亿三千万年前,而非一亿五千万年前,洛夫克拉夫特在《超越时间之影》里也犯了类似的错误,不知原因为何。]
在海底生活需要使唤修格斯,但它们在培育和管理修格斯时却遇到了新的麻烦。远古者们在雕画里悲伤地承认,随着时间的推移,从无机物中创造新生物的技术已经遗失了,所以它们只能改造那些已经存在的生物。陆地上的巨型爬行动物很容易驯服;但海里的修格斯,不仅能依靠分裂进行繁殖,而且偶尔还会表现出非常危险的智力。
什么智械危机!
剧透折叠(外星入侵)
到了侏罗纪时期,远古者遇到了新的麻烦——另一种新的来自外层空间的入侵者。这一次是一种半真菌、半甲壳类的生物——北方的某些山野传说也提到了同样的生物[注],而在喜马拉雅山脉地区,它们被称为“米·戈”,或者可憎的雪人。为了与米·戈开战,远古者们准备在地球周围的外层空间展开突袭。这是它们登上陆地后第一次试图回到宇宙里;然而,尽管像很久以前一样做好了所有准备,它们却发现自己已经无法离开地球大气层了。不论它们曾掌握着怎样一些有关星际旅行的古老秘密,到了这个时期,远古者族群已经遗忘了那些知识。最后,米·戈将远古者赶离了所有位于北部的大陆。但是,它们似乎无力去打扰那些生活在海里的远古者。渐渐地,远古者们开始一点点缓慢地向它们最初的南极聚居地退缩。
[注:见《暗夜呢喃》]
研究过那些描绘战争的雕画后,我们好奇地发现,构成克苏鲁眷族与是米·戈的东西与我们所知道的、构成远古者的物质完全不同。它们能够进行某些变形与重组过程,而它们的对手却完全做不到这些,因此这些外星种族似乎源自宇宙空间中那些更加遥远的深渊。而远古者,除开它们非同寻常的坚韧躯体和极为独特的生命特性外,依旧是由物质[注]构成,因此肯定源自我们所知道的时空连续体——然而其的生物的最初起源就只能留给我们去焦虑地揣测了。当然,这种假设的前提是那些入侵外敌所具备的特异能力,以及与地球毫无关系的特质,并非是纯粹的神话。可以想象,远古者们可能创造了一个宇宙体系来解释它们偶尔的战败,因为对历史的兴趣与自豪显然是它们最主要的心理特征。耐人寻味的是,它们的编年史里并没有提到许多曾出现在某些神话里、先进而强大的种族——那些晦涩的传说里曾一再提到过它们强大的文化与高塔林立的城市。
[注:此处用的是material,而描述米·戈与克苏鲁眷族用的是“matter” (涵义更广泛) ,洛夫克拉夫特想表达的是,远古者依旧遵守基本的物理定律,因此是物质的(material),而米·戈与克苏鲁眷族能够不遵守某些物理定律(例如克苏鲁能够变形和重组,米·戈的形象无法被相机捕捉)因此并非完全物质的只是东西(matter)]
这是它们登上陆地后第一次试图回到宇宙里;然而,尽管像很久以前一样做好了所有准备,它们却发现自己已经无法离开地球大气层了。不论它们曾掌握着怎样一些有关星际旅行的古老秘密,到了这个时期,远古者族群已经遗忘了那些知识。
氪星人?
疯狂山脉6
剧透折叠
我们进入的那座建筑物非常巨大,而且装饰得也非常精巧。这让我们对那一时期的建筑风格有了非常难忘的概念。虽然内部的隔墙不如外墙那样厚实,但建筑中较低矮的部分却保存得极好。整个建筑的最大特征就是如同迷宫一般复杂,而且每一层都会出现一些豪无规律的古怪变化;如果没有在身后留下撕碎的纸片作为标记,我们肯定会在一开始就完全迷失方向。我们决定先探索建筑物更加残破的上半部分,于是在这座迷宫里向上攀登了大约一百英尺,抵达了那些位于最高层的房间——那些残破的房间里满是积雪,屋顶已经不见了,只留下向着极地天空敞开的巨大空洞。建筑物内修建着许多带有横向棱纹的石头坡道,或者斜面,可供我们上下。这些建筑应该对应着我们经常使用的楼梯。旅途中遇到的房间,涵盖了任何人类能想象得到的任何形状与比例;从五角星形到三角形到完美的立方体。保守估计,房间的平均建筑面积约为三十乘三十英尺,高二十英尺,但也有更大的房间。在详尽地检查完上层建筑后,我们开始向下探索,一层又一层,深入那浸没在冰层之下的部分。很快,我们便意识到自己走进了一个连绵不断的迷宫——这座迷宫由无数相互连接着的房间与通道组成,甚至可能能把我们领向这座建筑以外的无穷空间。身边所有东西全都显得无以伦比的巨大与厚重,给人以一种古怪的压迫感;这些古老石头建筑的各个方面——轮廓、尺寸、比例、装饰乃至结构上的细微差别——全都暗含着某种模糊但却与人类完全不同的意味。不久,我们便从墙上的雕画里了解到,这座可怕的城市已经存在有数百万年了。
我们不知道城市的建筑者们利用了怎样的工程学原理调整那些巨型的岩石,让它们能够保持在怪异的平衡状态,但拱形结构显然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看到的房间全都是空的,没有任何便于携带的东西。这种情况让我们更加确信先前的结论——城市里的居民有计划地抛弃了自己的家园。几乎无处不在的墙面雕画构成了建筑装饰中最显著的特征。雕画通常都凿刻在连续不断的横向宽板上。这些横板的宽度为三英尺宽。除开雕画横板外,还有一种同样宽度的横板,这些横板上雕刻的是几何对称的蔓藤花纹。两种横板相互穿插,交替出现,一直从地板排列到天花板,占据了整个墙面。虽然我们也看到了其他的排列方式,但这种设计占了绝大多数。不过,我们也经常看到某块雕刻着蔓藤花纹的横板旁排列着一连串平整并且带有花边的圆角方框,方框里古怪地排列着一组组圆点。
我们很快就发现,这些图案所反映的雕刻技法非常成熟,创作者的技术也非常高超,其对于美学原理的把握更是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然而,这些雕刻里的每一个细节都与已知的任何人类艺术传统完全不同。就雕刻的精细程度而言,我还从未见过能与它们相提并论的作品。雕画采用了很清晰的比例,复杂植物与动物上最微小的细节也表现得栩栩如生,令人惊讶;另一方面,常用的设计也显得精巧而又纷繁复杂。那些蔓藤花纹展现了雕刻者对于数学原理的深奥运用——这些花纹均由复杂的对称曲线与折角组成,而且每种基本元素的数量都是五的倍数。雕有绘画的横板都遵循着一种严格定形的传统,并且对图案的远近透视进行了一种奇特处理,尽管它们与我们之间存在着漫长地质年代所形成的巨大鸿沟,然而这些图画所具备的艺术感染力仍旧深深地打动了我与丹弗斯。这些雕画创作者在设计构图时采用的基本方法是将所描绘事物的横截面二维轮廓奇怪地并置在一起——这表现出一种能够分析事物的心理特征,完全超越了任何已知的古代人类族群。若是将这些作品与我们陈列在博物馆里的那些艺术品进行对比,恐怕不会有什么结果。那些看过照片的人可能会发现与它们最接近的东西反而是那些最为大胆超前的未来主义者所提出的某些怪诞构想。
刻有蔓藤花纹的方框完全由凹陷的刻线组成。在未被风化的墙面上,这些刻线深度能达到一到两英寸。而那些刻有一组组圆点的圆角方框则会整个陷入墙面。这些方框内的平面会陷进墙面一英寸半的深度,而圆点部分则会再向下陷入约半英尺——那些圆点显然是用某种未知的远古语言与字母书写的铭文。带图案的横板采用的是下沉式的浅浮雕[注],浮雕的背景通常距离墙面有大约两英寸的深度。我们发现有一些雕画残留着上色的痕迹,但是大多数雕画上的颜料早已在无穷无尽的岁月中分解剥离了。我们越研究这些了不起的技法,就越是钦佩这些作品。虽然这些雕画有着严格统一的创作规则,但我们仍能领会那些艺术家细致而精准的观察与绘图技巧;事实上,那些惯用的创作规则本身就在象征与强调事物的真正本质,或者用来表现所描绘物体之间的重要差别。我们发现,除开那些能够辨认的优点外,这些雕画里还藏着一些我们无法感知的东西。各处发现的痕迹都隐约暗示着一些象征与刺激——也许在了解了另一种精神背景或文化背景后,借助更全面的——或者完全不同的——感官,才能让我们了解那些更深层、也更强烈的意义。
[注: 原文是countersunk low relief,其实是一种结合了浮雕和沉雕特点的雕刻工艺。创作者先将雕刻内容画在材料表面,然后凿掉没有内容的部分,然后再用浮雕的方式进一步细刻。这样制作的作品整体陷入材料内部,但有画面本身依旧是浮雕。国内似乎将这种方式归类为浮雕的一种。]
那些雕画的主题显然都源于创作者们在那个早已逝去的时代里的生活,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显然都是它们的历史。这个古老的种族对于历史有着超乎寻常的热衷与执迷——虽然只是巧合,但却为我们创造了一个极其有利的环境——它们的执迷使得雕画为我们提供了叹为观止的丰富信息,也让我们忘记了其他考虑,一心想把它们拍成照片、誊写在纸上。在某些房间里会出现地图、星图以及其他一些尺寸较大的科学图案,随着这些图画的出现,雕画的排列方式也会跟着发生变化。这些科学图案为我们从刻有绘画的横板与墙裙上了解到的信息给出了简单而又可怕的证实。在说明它们到底揭露了什么信息前,我只希望自己的叙述不会在那些完全相信我的听众心中唤起过份强烈的好奇心,至盖过应有的理智与谨慎。如果我的警告反而更加诱惑人们向往那块充满了死亡与恐怖的过度,那实在是个悲剧。
高大的窗户与十二英尺高的厚实大门穿插在满是雕画的石墙之间。偶尔,我们也能发现一些残留下来、早已石化的木门或窗户遮板——那些木板全都被雕刻上了精巧的图案,并且进行了抛光处理。所有的金属固定物早在很久以前就已经完全锈蚀了,但是有些大门还保持在原来的位置上——当我们从一座房间进入另一座房间时,常常不得不将这些木门推到一边。有时我们还能发现一些装着古怪的透明薄片的窗框——这些薄片大多数是椭圆形的——但数目并不多。另外,我们还常常能看到一些非常巨大的壁龛,大多数都是空的,但偶尔也有一些用绿色滑石雕刻的奇异物件——有的已经破损了,有的可能是因为太微不足道所以没必要一并带走。房间里的其他孔洞显然与过去存在的某些机械设备有关——供暖、照明,等等诸如此类——许多雕画中也展现过这些东西。天花板一般是平整的,但偶尔也会镶嵌上一些绿色的滑石或其他地砖,但大多数装饰都已经掉下来了。有些地板上也铺设着类似的地砖,但绝大多数地方都是平整的石板。
我之前已经说过,所有的家具以及其他可以移动的东西都不见了;但雕画仍让我们对于这些响彻着回音、如同坟墓一般的房间里曾经摆放过怎样一些奇怪设备有了清晰的概念。冰盖以上的楼层里通常都堆积着一层厚厚的碎石与岩屑,但是越往下走,这样的情况就越少见。某些位置较低的房间和过道里只有些许沙砾般的灰尘,或是古老的积垢,还有些地方甚至像是新近打扫过一般干净无暇,充满了神秘气氛。当然,在出现裂缝和发生倒塌的地方,位置较低的楼层也与上方楼层一样杂乱不堪。由于我们所进入的这座建筑里有一片中央庭院——我们驾驶飞机时也在其他建筑里看到过类似的结构——所以建筑的内部并不是一片漆黑;所以,在位置较高的楼层里,除非要研究雕画的细节,否则我们会尽量避免使用手电筒。但是在冰盖以下的楼层里,光线会便变得非常昏暗;在那些贴近地面、结构错综复杂的楼层里,大多数地方几乎是漆黑一片。
计划撤离的“远古者”们留下巨大的城市建筑。环境描写细致,使用一些显示矛盾的形容词以表示怪诞的形象。
但是,日本人类学者采纳这一论述之后,赋予其新的色彩。留下了史前遗迹的居民是“未开”民族,而外来的日本人则是摆脱了野蛮的征服者,人种的交替实际上是优胜劣汰的过程;这既和“记纪神话”的“神武东征”对应,也与当时风靡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密切结合。同时,将日本人与更早的居民割裂开,也就是将古老的野蛮人作为“他者”,树立起新的自我。
如前文所述,确实具有非常明显的殖民主义烙印。
日本近代人类学与殖民侵略的共谋,正如两部著作所揭示的,其方式是借由共通的术语、概念、制度来生产知识,要害在于过程而非结果。也就是说,即使学者的具体观点和当局所提倡的并不相同,然而没有意识形态根本上的断裂的话,依然助推了极端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未参与战争者,也可能要承担战争责任,是这段历史留给全人类的沉痛教训。
田中芳树直呼内行!
田中在其科幻军事小说《银河英雄传说》中提及了类似的观点:“会将好战的独裁者选成领袖,选民也不算纯洁无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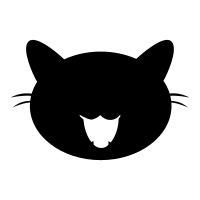 1·1 year ago
1·1 year agoperfect~
i just start a new group which topic as read chinese (mandarin) book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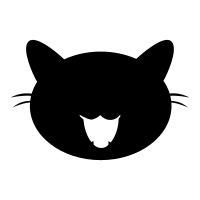 1·1 year ago
1·1 year agoMaybe there could be regional themes. Categorized by region.






重新点亮一盏灯
勃朗特姐妹早就知道文学领域一个不可忽略的事实:无论当时还是古代,女性作家都极少(牧师住宅的书架上没有简·奥斯丁的书),以三姐妹的天才,肯定明白社会对待女作家的态度,这自然诱发了她们的反抗,一个只属于家庭内部的反抗,哪怕这个家庭并不存在社会层面上的男女差异——当弟弟布兰韦尔确信自己将取得辉煌的文学成就时,夏洛蒂在想象的玻璃镇给予了无情的抨击,米勒解释为“她感受到威胁与排挤”(第5页)。夏洛蒂的感受是对的。这种家庭内部的反抗表明,社会生活中男女权力关系的结构,从最基本的家庭层面,延展到了“孩子”这一更基础的层级。后来,她在男作家处遭受讥诮与打击,不过是布兰韦尔行为的社会性演绎——一个家庭孩童矛盾的放大版,而夏洛蒂奚落、抨击弟弟的心理行为,与她此后面对男性群体误解时做出的反应保持了连续性,只是在“自我否认”的社会性层面下,后者更隐晦地出现在《维莱特》《谢利》等作品中。领取创作家的角色,并将之带入想象世界的行为,既在一方面证实了三姐妹 “加入这个神圣群体的渴望”(第3页),同时也是她们取男性笔名闯入文学界的开端。“三位虽然孤独却不乏雄心的约克郡家庭女教师以富有尊严的匿名形式,变成了柯勒·贝尔、埃利斯·贝尔和阿克顿·贝尔三兄弟,这一行为构成了一个集体的、宣告家族身份的行为。”([美] S. M. 吉尔伯特、苏珊·古芭:《阁楼上的疯女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319页)关于这一行为,人们很容易归结到概念性的性别问题上,米勒的史实性处理显示出在更早阶段、更具体的条件下,它已初见端倪。勃朗特姐妹无意陷入重重的性别困境,于她们而言,艺术更重要。
社会缩影。
社会视野
小说家盖斯凯尔太明白戏剧性技巧的重要性,她“把三姐妹的生平故事用作一个策略,分散人们对她们的作品中惊世骇俗的内容的注意”(32页)。通过这样的方式转移社会对三姐妹的批评,以实现对她们的保护,而同时,在写作过程中有意地将三姐妹的父亲、弟弟塑造为近乎“恶人”的形象,以证明三姐妹的不幸,此一处理,并非为了证明三人的不屈不挠,而是以一种更低的姿态,求取世人的宽恕。作为一个称得上成功的女性作家,盖斯凯尔又太明白应该如何去做这样的公关了——她所提供的人物,尤其女性人物,是不可以那么“自我”的,这一点已深入她的自我意识,甚至成为她的艺术自觉。当夏洛蒂创作《维莱特》时,盖斯凯尔正同步创作《露丝》,后者选择了一个具有争议性的主体,由于担心公众无法接受一个堕落女人作主角,哪怕这个女主人公善良到显得无知,盖斯凯尔还是要求夏洛蒂延期发表《维莱特》,米勒解释到,“这也可能是因为她不想与‘粗俗的’柯勒·贝尔被当作一丘之貉”(72页)。夏洛蒂小说中那些女性的强大“自我”自不必说,而盖斯凯尔作为一个自诩的“健康的人”“朋友”,则以另外的姿态,回避了自己的“朋友”。盖斯凯尔的艺术自觉使她知道怎样的女性才能为社会所接纳,她明白这个社会更看重作为女性的三姐妹的苦难,而不是她们文本中“自我”冒犯的成就,她要展现她们的不幸,并将之悲剧化。进一步说,盖斯凯尔的眼光是一种男性的眼光,是社会的眼光。于是,当她为夏洛蒂三姐妹作传,一个“家庭天使”“殉道者”的圣人形象,被树立起来了。
当代写作者也时常有这种“虐女”或“乞怜”的迷思。